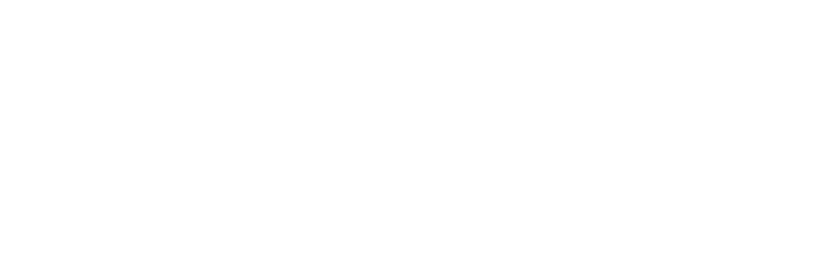作者简介

孟庆国
主要研究政府治理与创新,电子政务与数字政府,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承担了近七十余项的国家级课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执行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电子数据治理工程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治理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报告摘要
一是分析《“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回顾数据要素政策的演进脉络,介绍数据要素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产业新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从而实现对经济发展倍增效应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二是解读文件的主要内容,剖析总结文件呈现出的一些特征。从为什么是数据要素乘×;数据要素发挥价值的供给、流通与应用三个环节;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中平衡理念与原则;数据要素潜能释放的三个途径等内容特征上,剖析数据要素化的开发利用问题。
三是思考和体会。从数据要素释放价值途径、数据关联对象决定权、数据产品化确权三方面,分析了行动计划执行推进中要把握的问题。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把数据上升为国家级战略不单是在我国,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把数据作为赢得下一轮产业竞争优势、保持国家综合实力的国家战略。在我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率先提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论断。数据要素这个概念在我国被率先确立,也表明在数据要素探索上我们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围绕数据和数据要素,我国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文件。对于这些政策文件和法规,可以从两个视角来比较概括:一是保障安全方面的;二是促进发展方面的。“行动计划”是促进发展政策谱系的最新文件。该文件将“数据要素”视为一个具有倍增效应的驱动因素,通过该文件的政策形式,来推动数据要素在十二个典型行业领域发挥赋能作用,进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乃至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
把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把数据要素列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就意味着数据在国家制度和政策设计中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赋能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即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生产要素的应用。针对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作用,已有很多的研究,尤其是和传统生产要素的类比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相比,由于其特征的巨大差别,在其开发利用中“供给-流通-应用”机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文件(又称“数据二十条”)。
在“数据二十条”的基础上,为了让数据要素能够与各行各业紧密融合,国家数据局等十七个部门又联合印发“行动计划”。从总体要求、重点行动、支撑保障等方面,系统部署了数据要素在十二个重点行业领域的落地工作。如果说“数据二十条”是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那么“行动计划”则是在这个顶层框架指导下的落地实施指南。
按照文件要求,我国各个地方也在快马加鞭地推进政策的落地工作。一是推动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立与改革工作。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地级以上的地方政府会全面设立数据管理机构。二是成立数据集团,推进数据的供给、流通和开发应用。为了让数据资源能够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很多地方成立数据(产业)集团、数据交易所等机构已成为必然选项。
正是上述文件的发布和实施,加上数据管理和运营机构的成立,使得我国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走向了快车道。“行动计划”优先选择了十二个重点行业领域来推进数据要素化政策的落地工作。这十二个行业也是我们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率先探索出有利于发挥数据要素赋能作用的路径,无疑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文件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文件内容包含五个部分:1.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2. 总体要求;3. 重点行动;4. 强化保障支撑;5. 做好组织实施。其中,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中,明确了数据要素工作目前面临形式和开展“行动计划”的意义。“重点行动”构成了文件的主体内容,从十二个典型行业领域,部署了“行动计划”和内容。文件通篇体现了数据要素“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
文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文件强调了数据要素的“×”,而不是像过去互联网用的“+”。对数据要素的“×”,大家都很关注,网上有很多的讨论。为什么数据要素是“×”?我们认为,用“×”,这不仅突出数据要素自身的价值,更凸显了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倍增、叠加和放大效应,即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价值倍增效应,即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相融合带来的乘法效应。这种倍增效应是数据自身的零成本复制、多场景复用等本质特征决定的。
第二个特征,文件强调了数据要素发挥价值的供给、流通与应用三个关键环节。文件多次强调要推动数据供给,通过提升数据质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让数据“供得出”。其次,文件强调优化数据的流通环境建设。通过完善市场化机制,如构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促进公共数据的流通。要盘活数据资产,让数据“流得动”,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制。再者,结合十二个具体行业领域,文件强调了数据的应用,力求让数据在这些典型行业“用得好”。
第三个特征,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中,文件强调和注重了平衡的理念和原则。包括:数据供给和数据需求的平衡、数据发展和数据安全的平衡、数据开发利用中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数据价值与收益分配的平衡,以及数据合规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第四个特征,文件强调了多要素协同、多主体复用、多数据融合释放数据潜能的三个途径。多要素协同,指的是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传统要素的相互协同,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倍增。多主体复用,指的是在数据开发利用中,强调同样的一个数据(集)可以用在多个场景,也可以被众多主体多次复用。这个数据不单单你能用,他也可以用,甚至大家都可以获取使用。那么,构建一个公平的、有序的、可以促进数据有效配置的生态体系就尤为重要。多元数据融合,就是指的来自不同主体、不同系统、不同平台等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关联、匹配和融合使用。比如,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企业数据在企业间的共享使用等。所以,要建立起数据价值释放的途径,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这三种途径尤为重要。
我们分别以一个例子予以进一步解释和阐明。在多要素协同方面,北京市开展的金融专区探索,在多要素协同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在多场景和多主体复用方面,在城市大脑中的实时公交应用是典型的数据复用的例子。在多元数据融合方面,“航旅纵横”把航班数据和机场、酒店、网约车等数据进行合作和打通,创新出了独特的数据利用商业模式。
三、几点思考与认识
一是数据要素释放价值途径的再认识。
在现实中,由于受传统要素思维的影响,认为一个机构所拥有的数据资源,可视为该机构的资产,这些资产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变现。事实上这些数据资源不会自动变现,也不会自我产生价值,更不是像萝卜白菜那样按斤叫卖获得收益。就像数据不会凭空而存在,是产生于各类场景应用中一样,数据的价值实现也必然在各类场景应用中产生。数据是在一定的场景中,通过和和传统要素的融合产生价值。
例如,数据与土地要素相融合,可以通过各类数据挖掘分析,使土地资源得到更优配置,从而让土地要素价值倍增。一些地方城市大脑建设中推出的停车指数应用,可以极大化地优化配置城市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再如,利用ChatGPT工具,可以节省文稿的处理效率也就是说,采用大数据训练出来的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场景中,直接将人的工作效率提升了数倍。所以,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一定是在与传统要素融合中产生的,是通过多要素的融合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巨大提升。
二、是不能忽视数据关联对象的决定权。
不论“数据二十条”,或“行动计划”,我们都认为是在考虑数据主体集即数据关联对象决定权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因此在推进数据要素化工作中,一定不能忽视数据关联对象数据原始决定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数据关联对象的授权是数据开发利用的前提,不管是非敏感数据,还是隐私或商业秘密等敏感信息。按照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的内容要求,数据关联对象的决定权可以视为高于数据资源持有权,也高于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所以,在推进按数据要素化工作中,包括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数据主体的决定权是数据开发利用的前提。具体怎么保障和行使这个决定权,还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应用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数据要素化绕不开数据的确权问题。
推进数据要素化工作,核心是数据资产化问题。既然将数据视为新型资产,那么如何与现有会计准则相衔接?是对原始数据进行资产化?还是将数据产品进行资产化?我们的观点是,现阶段对原始数据进行资产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相对而言在数据产品层面上进行确权授权有很大可行性。所以,很多专家的观点和地方的探索越来越聚焦到数据产品的确权授权上,即通过数据产品化确权而不是对原始数据确权来推进数据要素化和数据资产化问题。我们清华大学和中国电子联合推进的“数据元件”的概念,就是基于对原始数据的加工处理,形成可确权、可计量、可定价、可流通交易的数据中间态产品,来推进数据的要素化问题。
本文来源网络,侵删。